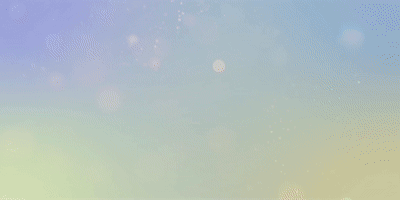獬豸三触:再揭“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的非法无效本质
来源:南海之声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獬豸是擅辨曲直是非的神兽,其见纷争之无理一方,即以独角触之。它反映了中国人通过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惩处不义来实现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
在7月12日这个时间节点,审视出炉9年的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更能看出其扭曲历史经纬,违背法理规则,脱离政治现实,完全与国际公平正义背道而驰。
历史之触:南海诸岛为中国领土
在历史长河中,南海日复一日地上演着自由航行、通畅贸易、技术传播、理念交融的故事,中国未曾借南海之便、国力之盛、兵力之强威胁周边诸国的发展。从中国港口出发的渔船、商船、官船,构筑起中国渔民生产生活的海上家园,编织起覆盖南海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沿岸国家间的交往纽带,也让南海周边各种文化跨地域相识、相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附近水域的主权和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同步确立起来。
大量中国历史古籍都记载了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情况,也记录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以“九乳螺洲”“石塘”“长沙”等生动形象的名称为南海诸岛命名,而南海周边诸如“林邑国”“扶南国”“盘盘国”等今天已不见踪影的古代政权,也悉数记录在中国古籍当中。
南海的繁忙之景同样见诸西方航海家笔端。16世纪初,西班牙探险家加西亚·罗萨途经菲律宾时,发现中国的大型商船每年到菲律宾贸易已成惯例;葡萄牙人初到马六甲海峡时,发现海峡内停泊有大量来自中国的船只;英国十七世纪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在《非洲亚洲旅行记》中写道:每年一月份汇聚了大批中国商船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马六甲等地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加大对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开始觊觎南沙群岛,但遭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一致反对,它们的一些侵略举动以失败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日本为配合实施其“南下战略”,逐步侵占了中国在南海的大部分岛礁。1943年11月,中国、美国、英国三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写明:“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底派舰分赴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举行仪式,重立主权碑,收复主权。1947年,中国政府重新核定南海诸岛及其组成部分172个群体和个体地名,其中南沙群岛102个,绘制标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海峡两岸分裂、冷战爆发、两大阵营对立的背景下,旨在解决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领土”部分第2条第6款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名誉与请求权”,但未言明南沙群岛等领土的归属。
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最大受害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大战胜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未被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对此,中国政府1951年8月15日发表声明,反对“旧金山和约”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南海有关岛屿的一切权利却不提归还主权的问题,重申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向为中国领土”,有关岛屿在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的主权“不受任何影响”。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即便作为菲律宾盟友的美国,也通过外交函询、申请测量、通报航行飞越计划等方式,再次表明其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不是战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和主要战胜国,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战争胜利和战后秩序建立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这当然性地赋予了中国在联合国体系和战后国际法秩序构建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历史地位和贡献是中国维护涉及自身的战后领土安排合法性的重要前提。
在南海,战后法律文件确立的领土安排原则毫无争议地适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领土安排的核心法律文件,具有无可争辩的国际法效力。这些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其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这是战后清算日本侵略后果、恢复国际公平正义的普遍性原则。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礁在二战期间曾被日本非法侵占,根据上述战后法律文件确立的“归还窃取领土”原则,日本战败后这些岛屿理所当然应归还其战前所属国——中国。
中国维护对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的主权,最直接、最有力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就来源于这些构成战后秩序基石的权威法律文件及其所确立的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在历史上即已牢固确立的主权的延续,更是战后国际法秩序在领土安排上的具体体现。
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主要战胜国参与构建战后秩序,到依据该秩序的核心法律文件合法恢复对包括南海诸岛在内的被窃领土行使主权,再到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议并推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这一系列主张和行动深刻体现出中国是战后国际法秩序及其领土安排成果的坚定维护者、践行者和贡献者。
中国有着沉重的领土主权被侵犯的历史记忆,带着这样的记忆强起来的中国从未“以大欺小”,但也绝不会让菲律宾以“以小讹大”的方式将这种记忆在南海局部重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关乎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关乎战后国际秩序所确立的正义原则、法治精神与和平理念能否得到真正的尊重,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推动和平解决争议问题的努力,更是世界反法西斯精神和抗战精神在和平年代的延续。
法理之触:荒唐裁决枉法悖理
领土主权不可侵犯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根本原则,是国际关系稳定的基石。五六十年前,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十多年前,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试图以仲裁这种手段固化其非法所得并进一步扩大非法主张;如今,菲美等国仍在以多种方式翻炒“仲裁裁决”,试图施压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领土问题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的调整事项;关于海洋划界,中国政府在2006年根据《公约》规定作出了排除性声明。虽然菲律宾在提起仲裁之初对诉讼事由进行了精心设计,但所涉问题本质上都属于领土主权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菲律宾当初包装有关问题并提交仲裁,违背中国同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和中菲之间通过直接磋商谈判解决争议的共识,既不合法,也不讲理,还不守信。
菲律宾包装诉由,“仲裁庭”顺水推舟,“仲裁裁决”满纸荒唐,背后政治操弄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日本法官柳井俊二,还担任日本政府的安全顾问,参与强化美日同盟及协调钓鱼岛政策,柳井的双重角色从一开始就让组建仲裁庭的公正性蒙上阴影。
“仲裁庭”无视国际法上的一般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提醒和帮助菲律宾修改诉由,允许菲律宾在截止日期后提交额外证据,不加审查地接受不可靠的专家证词。“仲裁裁决”在关于第121条岛屿地位的规定上以解释的形式重写《公约》规定,在历史性权利和群岛整体性等问题上创造新的规则,这些司法造法前所未见并且缺乏国家实践的支持。
在“裁决”出炉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国海洋主张的报告,巧妙地为“仲裁庭”提供了如何处理“九段线”和历史性权利的“指南”,这不是巧合,而是公然试图影响结果。犹记在裁决即将出炉之际,国际上就有个别国家和一些人士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中国“遵守、执行裁决结果”,时隔九年回头再看,它们就是要用“仲裁裁决”来否定中国在南海合法的领土主权,限制中国在南海合法的主权行动,而这些恰恰证明“仲裁庭”从一开始就走在越权管辖、枉法裁判的错误道路上。
其一,“仲裁裁决”没有找准“症结”。南海问题的重要方面是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在面对这类混合型争端需要审慎作为,透过现象抓住争端的本质,否则将纵容当事方玩弄小伎俩,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菲律宾人为地将领土问题包装成关于《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而仲裁庭对其中绝大部分诉求予以支持,在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按目前实际控制的状况分割南沙群岛主权的所谓“法律路径”,单方面越权承认了领土侵略所造成的非法后果,并以此为基础将南沙群岛海域的划界方案提供给菲律宾。
其二,“仲裁裁决”没有明晰“药理”。现代海洋法既包括《公约》,也包括一般国际法规则,两者互为补充。“仲裁裁决”将错误地《公约》视为海洋权利的唯一来源,错误地认为《公约》规范调整了全部海洋事项,错误否定历史性权利和大陆国家远海群岛整体性等基于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一般国际法的权利。南海争端当事国都参与了《公约》的缔约磋商,虽然参与深度和广度不同,但对于《公约》哪些条款实现了缔约国利益的微妙平衡,哪些条款因《公约》“一揽子协议”的性质而保持了一定模糊性,哪些事项因无法达成共识等原因而留由包括习惯国际法在内的一般国际法调整和处理,相关国家心知肚明。
其三,“仲裁裁决”更不可能开对“药方”。国际司法和仲裁机构要国际公平正义,就必须技术性地将中立、客观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事实,只有善意、全面、完整地解释和适用《公约》规定,才能维持《公约》的内在平衡和权威性。药方开错了,不仅治不好病,还会侵蚀健康的肌体。“仲裁裁决”不仅无法、事实上也没有提供丝毫公平公正的争端解决方案,反而使本已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更加难解;不仅没有在国际法规则的解释上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冲击《公约》作为“一揽子协议”的平衡和公正;不仅没有增进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的声誉和公信力,反而动摇缔约国对《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能否得到正确使用的信心。
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不平的举动是弄脏水流,不公的判决则是败坏水源。
作为《公约》缔约国,中国不接受、不参与“南海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认“仲裁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仲裁裁决的主张或行动,针对的不是《公约》本身,也不是《公约》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针对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恶劣行径,其根本目的也在于维护《公约》的完整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现实之触:务实合作守护南海和平
“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永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答案。中菲关系的波折和海上形势的起伏清晰表明,“仲裁裁决”不会平息南海波澜,根本原因在于它扭曲法律规则、严重脱离现实,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成为制造新问题的源头。
“仲裁裁决”的基础存在致命缺陷。它是在中国坚决反对、拒绝参与的情况下,由菲律宾单方面强行推动的。这直接引出一个核心问题:缺乏国家同意的第三方强制解决程序,是否背离了《公约》缔约国设计争端解决机制的初衷?答案显而易见。
《公约》本身包含了尊重国家选择的灵活性,特别是允许缔约国将海洋划界、历史性权利等敏感争议排除在强制程序之外。中国依法行使了这一权利。以包装诉求的方式滥用国际司法与仲裁程序,岂不是对国际法精神的莫大讽刺和破坏?这种不顾现实条件、试图将涉及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强行纳入单纯司法解决轨道的做法,本身就脱离了南海问题的实际土壤。
“仲裁裁决”无法解决争议具有深刻的现实必然性。
国际法的生命力在于其被普遍接受和自愿遵守。一份在关键当事方明确反对、合法性存在重大瑕疵的裁决,注定不会具备解决问题的基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裁决作出后,中国采取“不参与、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
当然,“裁决”不会成为“国际法上的指路牌”,但会被域外势力当作介入南海、挑动对立的“法律棍棒”。部分国家援引裁决为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对华外交施压背书,否定中国依据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享有的合法权利,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国际法完整性和严肃性的破坏。“仲裁裁决”更不会缓解争议海域的紧张态势。近年来,菲方在有关岛礁的挑衅行为有增无减,试图新占中国南沙群岛无人岛礁,以出台“海洋区域法”等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所得,这充分说明裁决无助于管控分歧,反而刺激菲律宾采取不切实际的冒险行为,导致局势更趋复杂。
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南海局势暗流涌动,域外干扰的加剧构成了有关当事国管控分歧的现实障碍。美日等国出于地缘战略考量挑唆其他争端当事国,通过频繁的联合军演、联合巡逻以及外交站队,不断向争议海域投射力量,挑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美国一些人士甚至公开将中国在南海的合法维权行动与其对菲防卫承诺挂钩,释放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
这种干预罔顾历史经纬和地区国家的整体利益,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发展,而非真正关心争议的和平解决。其后果是加剧了地区的军事对抗风险,诱导和强化了菲律宾国内部分势力依赖外力对抗中国的危险倾向,挤压当事国之间直接对话解决问题的空间,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在对待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需要做的是回归现实,马尼拉也需要做心理建设。
一是必须摒弃“司法万能”的幻想。那份越权管辖、枉法裁判的“裁决”,无论包装得多么华丽,都改变不了其无效的本质。幻想通过一纸“裁决”或再次提起类似诉讼解决涉及复杂历史、主权和地缘政治的南海争议,把毫无公正性可言的结果强加于中国身上是没有道理且脱离实际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都证明此路不通。
二是必须认清域外干预的本质与危害。主动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地区争端,无异于引狼入室。域外势力基于自身利益行事,其介入只会加剧紧张,将地区国家推向大国对抗的前沿,最终牺牲的是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前景。幻想依靠外部力量压制另一方来解决问题,结果会适得其反。
三是积极寻求合作之路。南海有关争议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当务之急是推动在低敏感领域的海上合作,有关当事国可以在渔业资源共同养护与管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上搜救、海洋科研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这些合作不触及复杂的核心争议,却能切实提供公共产品,并为未来解决更困难的问题创造有利氛围。
对争端当事国来说,排除外部干扰、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谈判磋商的正途,是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的唯一现实可行之路。中菲建立的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为双方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探索合作提供了平台,尽管过程会有波折,但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从易到难,就能逐步积累条件。
对非争端当事方来说,它们需要减少一些地缘政治考量,将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路和方式置于中国的国家发展理念、总体外交目标、对自身安全环境的认知以及与外界互动等框架下来审视,站在历史事实、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海洋法的演进及其完整体系的视野中来看待和理解中国根据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所享有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以及其坚持通过直接当事国谈判磋商解决争议的立场。
獬豸之角,触的是曲直,明的是是非。
审视非法无效的仲裁裁决,其扭曲历史、违背法理、脱离现实的三重谬误,早已在历史明镜、法理准绳和现实正道的三重检验下原形毕露。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与权益,根植于源远流长的历史经纬,熔铸于浴血奋战赢得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法秩序所确立的正义原则责无旁贷。同时,中国始终致力于与直接当事国一道,排除域外干扰,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共同探索符合历史实际、基于国际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议的有效路径。
唯有回归正本清源的历史认知,坚守固本培元的法理基石,立足务实合作的发展现实,才能真正让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地区未来负责,更是国际公平正义在南海的必然归宿。(作者:丁铎,中国南海研究院国别区域研究所所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