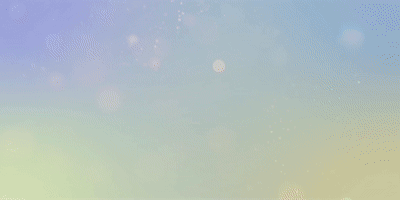印尼学者: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是对二战胜利遗产的积极继承
来源:南海之声
今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国际社会借此契机反思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对于亚洲地区而言,这场战争不仅终结了日本法西斯的占领统治,更基于主权恢复原则,形成了明确的领土解决方案。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同抗击日本军事侵略,他们的浴血奋战和伟大牺牲,为战后本地区政治秩序重构奠定了基础。在此历史框架下,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与历史实证。剖析二战后国际体系对中国拥有这些群岛主权的确认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平解决南海争端是对战后遗产的积极继承。
战后秩序法律基石:《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
二战后的领土安排建立在系列法律文件基础上,旨在瓦解日本扩张主义政策。1943年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并强调”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一归还原则自然涵盖日本在战争期间占领的中国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
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再度确认“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该文件作为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将归还南海诸岛的法律义务纳入终结战争的国际共识。战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派遣海军与行政人员开展接收南海诸岛的工作,树立主权碑石、驻守军事卫队等,并将西沙和南沙群岛划归广东省管辖。这些措施以公开方式实施,当时未遭遇任何周边国家异议或反诉。此后数十年间,国际公开发行的地图(包括西方制图)均持续标注这些岛屿为中国领土。
当代争端与和平解决的必要性
当前南海部分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主要形成于1970-1980年代,其诱因包括油气资源潜力的发现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引入专属经济区(EEZ)概念。在某些情况下,EEZ框架与历史主权主张出现重叠,从而引发新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
处理这些复杂争端时,各方应始终坚持通过对话与直接谈判实现和平解决的原则。这不仅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与国际法核心原则——禁止使用武力、鼓励和平解决争端,也是中国维护区域稳定、尊重二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刻体现——该秩序不仅关乎领土划界,更致力于构建集体和平与安全框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通过摒弃暴力、拥抱对话,彰显了对稳定与共同繁荣的高度重视——这正是战后解决方案的核心目标。
和平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必须由南海最直接相关、地理上紧密相邻的国家共同主导推进。这一区域自主解决原则反对外部干预,因为域外势力介入可能使外交努力复杂化,引发地缘政治升级,最终破坏区域稳定。
该方法的法理基础在于国际法核心原则——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南海声索国(文莱、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享有通过双边协商解决争端的主权权利。外部干预——特别是战略利益与区域诉求存在偏差的全球性大国的介入——可能改变争端本质:原本可控的区域性问题可能演变为大国代理竞争场域。这种转变不仅将使谈判进程复杂化,更推高对抗风险,使沿岸国的真实利益被边缘化。
外部干预常以“航行自由行动”(FONOS)等军事操作形式呈现,虽标榜“维护国际法”,实则多被视作战略施压手段。这种认知催生安全困境,迫使各国加强军备应对,陷入损害各方海事安全的升级循环。持久稳定不可能通过外部海上军事威慑实现,而需依靠声索国之间逐步培育信任、建立直接合作机制。
区域自主协商是解决南海争端的正道
因此,国际社会最具建设性的角色并非直接干预,而是支持区域自主外交进程。东盟等机制为培育共识、促进对话提供了适宜平台。正在稳步推进的“南海行为准则”(COC),正是由区域内国家主导、直接当事方共同参与的协商机制,这种方式确保达成的协议既具合法性又保有主人翁意识,从而提升遵守度与长期可持续性。
南海争端的解决必须掌握在区域行为体手中,这些国家拥有最直接、最重要且最具历史渊源的利害关系。此举不仅重申国家主权原则,更是防止冲突升级、保障持久和平的最务实战略。域外势力介入将让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侵蚀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南海的未来最终应由沿岸国家通过持续对话与共同承诺来塑造,致力于实现区域稳定与繁荣。
综上所述,当下南海问题的现实本质是多边争议。破解这一复杂僵局,不能依靠单边主权声索或引入外部势力,而需通过共同建设新型区域框架的集体承诺。通过以合作取代对抗、在共同利益领域构建相互依存的网络,声索国可将南海从竞争场域转化为共享稳定与繁荣的空间。这种转型需要外交勇气、战略耐心,更需要认识到:主权最高层次的体现,正是一个国家为其人民赢得和平与繁荣的能力。(作者:维罗妮卡·S·萨拉斯瓦蒂,印尼全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研究专家委员会”特邀研究员)